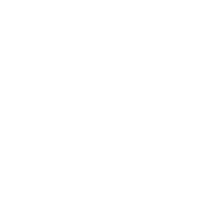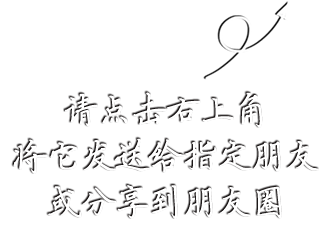文人潇洒写美食
新即墨
2021年09月22日
陈修远
我在家乡即墨工作的时候,就喜欢写一些即墨的美食,什么即墨麻片、大柳树包子,什么老郭的肠子、流亭的蹄子,什么好吃就溜溜达达地写什么。朋友见了面都笑话我说:“看看,我们的美食家来了。”更有甚者,有的人竟然称我为“大即墨第一馋”呢。
去年初秋,缘于一档电视栏目的撰稿,我们来到了美丽的苏州。这次来苏州,使我对“上有天堂,下有苏杭”这句话有了新的感受。人人都知道姑苏风光如诗如画,但是不知你是否留意,苏州的美食更是“如诗如画”,特别是苏州小吃,做得是如此精致、细腻、诱人,叫你看了就会有一种不得不尝一口的诱惑。源于什么?源于这里自古就是文人墨客的游聚之地,文人们吃得满嘴流油满心欢喜之余,剩下的就是谈诗着文乐陶陶然了。就这样,苏州美食陶醉了文人,文人成就了苏州美食,美食又成就了旅游,旅游又成就了美食……形成周而复始源源不断的美食文化。
于是我就想,出文人的地方,除了地灵毓秀,必然出美食,因为很多美食都跟文人有着关联。即墨自古不乏文化名人,从即墨大夫、王氏三代(王羲之的先人王吉、王骏、王崇),到周、黄、蓝、杨、郭,官声文名天下皆知。但似乎即墨古代的文化人对“吃”比较避讳,没有在即墨美食上留下诸如“兰陵美酒郁金香,玉碗盛来琥珀光”及“扬州鲜笋趁鲥鱼,烂煮春风三月初”的佳句。许是因于此,即墨很多传统美食,至今没能名扬四海而招引得八方宾客做客即墨,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。
当年,贺敬之先生的一句“杯接田单吟老酒”,着实为即墨老酒的宣传添上了巨翼;今天,范曾先生“妙府老酒”的浓墨题词,又使妙府老酒锦上添花,这就是文化的效应。记得那年有着“即墨太史公”之称的东崂先生,写过一篇《即墨猪头肉》,那即墨猪头肉让他写得叫人忍不住满嘴流涎,满肚子里的“馋虫”被勾得阵阵骚动,非得切上一大盘满口淤腮猛歹一顿方能过瘾。你看——“猪头肉本来就好吃,叫即墨人三捣弄两扎固就更好吃得了不得。这家伙一出锅,热腾腾,汤漉漉,油光光,快刀斩乱麻,切上一大盘,碰上以之为饭的大腹便便之徒,最好是切成满口货的四楞子块,然后浇上一蒜臼子酱油蒜泥,一拌拉,有点烀通辣气的不妨事;到此时,你便下筷子,直取那半肥带瘦的,满口裕腮,嚼它个嘴角淌油,腮帮子喷香;三五块过后,再来一盅老白干,吱溜一声,飞流直下,肉香酒香,溢满五脏六腑……”
于是我就想啊,即墨今天有很多的文人,他们对即墨的美食也是情有独钟,如果他们的笔触流淌出即墨美食的文字,那么我们即墨老酒、妙府老酒、即墨麻片、蜜三刀、老郭肠子、大过年饺子、大柳树包子,还有酒店的什么特色菜品食品饮品的,把那天南地北的宾客都馋来,让他们尽情品尝咱即墨的美食小吃,品尝咱即墨人的文化和智慧,品尝咱即墨的山山水水,到那个时候,即墨可真的就名扬万里了。
美食陶醉了文人,文人成就了美食,看看自古文人墨客,百世留名的,有几个的文章诗词歌赋中离得开美酒美食美景?李太白总结得最为经典:自古圣贤皆寂寞,惟有饮者留其名。
陈子亦曰:美食美景灵感至,妙笔生花传百世。墨城风流看今朝,文人潇洒写美食。陈子谓谁?即墨东乡钱谷山人士陈修远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