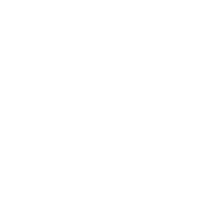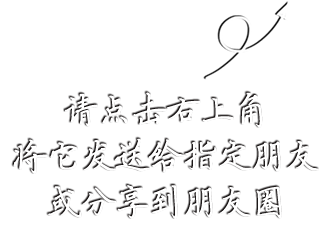小小蛤蜊,何以成夏日“顶流”?
新即墨
2024年06月19日

新即墨2024年06月19日04版面

黄辉 摄

宋云玲 摄
有人说,青岛人过夏天,有自己的“幸福三宝”:哈啤酒、吃蛤(gá)蜊(la)、洗海澡。
也有人说,“青岛人不是在哈啤酒,就是在打啤酒的路上;不是在吃蛤蜊,就是在挖蛤蜊的路上;不是在洗海澡,就是在去海水浴场的路上”。
这些说法虽带着几分调侃,却是青岛人日常生活的缩影,也反映了蛤蜊在这座城市的“江湖地位”。
蛤蜊,是百姓餐桌上最常见的小菜,是人们对那一口“鲜”的执念,也是一缕割舍不断的乡愁。它甚至成为一个文化符号、一种休闲风潮、一次全民大party,让人们笑开颜、爽翻天。
一
如果为青岛人的舌尖搜索一个关键词,那答案很可能是“蛤蜊”。游子思念家乡,古雅的说法叫“莼鲈之思”,而假如换成青岛话,可能就是“想吃蛤蜊了”。
读音里的“青岛印记”。在社交平台上,很多人分享来青岛旅游的印象,都会提到菜谱上的蛤蜊,“普通话明明读gé lí,青岛话却读为gá la”,单凭这个独树一帜的读音,就让他们记住了这座城市。其实,青岛方言属于北方方言里的胶辽官话,就像把“喝啤酒”说成“哈啤酒”一样,蛤蜊的读音中有本土方言的特色。
餐桌上的“那一口鲜”。穿行大街小巷,可以看到蛤蜊的“七十二变”。烤、炝、炒、爆、炸、烧、烩等一应俱全,有的西餐厅还推出了蛤蜊烘焙。青岛盛行的是原汁蛤蜊,做法很简单,就是放进锅里,盖上锅盖,不用说调料,连水都不加,拧开火就行。几分钟后,一锅蛤蜊开口对你“笑”,鲜气四溢,柔嫩多汁。剩下的蛤蜊汤也不会被浪费,用来煮面,鲜美无匹。还有人把蛤蜊倒入烧水铝壶,放在火炉上,最上面一层先开口,开一个吃一个,一层层吃下去,那叫一个鲜。
大海中的“著名物产”。蛤蜊个头较小,壳面光滑,有同心环纹,呈青白色,煮熟后会变成漂亮的浅褐色。据说,如同人类的指纹一样,世上也没有任何两个蛤蜊皮的花纹完全相同。
二
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民,一片泽海孕育一片生机。无论是“赶海挖蛤蜊”,还是“哈啤酒,吃蛤蜊”,都是青岛人特有的仪式感,是海洋文化在饮食上的烙印。
挖的是乐趣,也是渔盐文化。据考证,炎黄时期的东夷部落,是中国渔业的重要源头,而青岛地区所处的正是“莱夷地”。传说,东夷部落的首领郎君氏,在红岛海滩上结出了第一张渔网,被后人尊为“渔祖”。另一首领夙沙氏,成为用海水煮制海盐的鼻祖,被尊为“盐宗”。
品的是美食,也是生活情趣。蛤蜊的美味,古人早就发现了。西周时,蛤蜊是进贡王室的贡品。不少古人还是“蛤蜊控”。比如,欧阳修在扬州做官时,曾与宾客争食蛤蜊,“其食唯恐后,争先屡成哗”。苏轼、黄庭坚等人,把“食蛤蜊”当成口头禅,“谁能着意知许事,且为元长食蛤蜊”。大体意思是“算了,我们去吃蛤蜊吧”,相当于“吃瓜”的文学化表达。
在今天的青岛,通过吃蛤蜊也能管窥这座城市的群体性格。比如,热情好客。“来青岛找我,请你哈啤酒吃蛤蜊。”这是青岛人对外地朋友常说的话,只吃蛤蜊吗?当然不是,届时会有满桌的海鲜。再如,热爱生活。忙碌了一天,青岛人喜欢打一袋散啤,买两斤蛤蜊,花不了多少钱,就能开启一个美好的夜晚。
看的是烟火,也是岁月变迁。蛤蜊也是一扇窗口,里面有似水流年和城市发展。
三
时代的东风吹拂,小小的蛤蜊,长成大产业,玩出新花样,为餐桌加味,为生活添彩,为城市赋能。
“蛤蜊候风雨,能以壳为翅飞。”这是唐代段成式在《酉阳杂俎》中所写。这个“飞翔的蛤蜊”的意象,虽属误解,却别具浪漫色彩。当下,蛤蜊正肥,让我们在“山”“海”“潮”之间,品尝大海的美味,体验收获的乐趣,寻找生活的美学吧。
(转自青岛宣传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