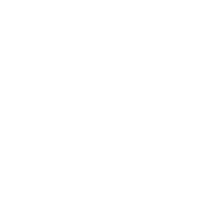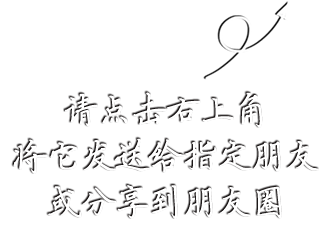赵丕山 :我的抗美援朝
新即墨
2022年08月05日


讲述人简历:
赵丕山,又名赵培山,即墨区北安街道刘家后戈庄村人。1932年出生,19岁入伍,1952年4月,赴朝作战志愿军后勤2分部独立营2连战士、步机枪手、副班长。1954年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,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,1957年4月复员。
解放前,我家里很穷,去要过饭,也给人家扛过活。共产党来了,斗地主,搞土改,我家分了两亩地日子才好起来。
1951年,我积极报名参军,还鼓动俺村三个青年一块去。
我快二十岁了,长这么大,数着共产党待我好,待俺家好,待咱们穷人好。“滴水之恩,涌泉相报”,咱得回报,没有共产党哪有新中国?
但是,刚解放那会儿,人的思想不一般齐呀。许多人对抗美援朝这个事有不同观点,有说东的也有说西的。地主、富农的孩子不能去吧?再说,你去部队还不一定要你来。还有的人小心谨慎,掉块树叶都怕打破头,你给他杆枪上战场能中?营上乡武装部迟部长挺看好我的,头着冬天就叫我报名,为什么呢?我是民兵骨干,工作积极,跟迟部长执行过好多次任务,有急难险重的差事只要安排我,领导们都放心。迟部长说:“丕山,国家有难,青年当先,你带个头吧。”我没打艮次,说:“好,我泼辣皮实,自己也觉得是个当兵的料。缺点呢,没上过学,没文化,但我听说当了兵也可以上学。”
回家还得做爹娘的工作,我说:“咱得去,都不去谁去?”爹娘思想开通,说:“你自己考虑,行,就去呗。”
那年正月俺村当兵的好一档子人来,有二三十吧。有邹伦先、李云石、薛正俭,有下疃村赵光远、黄立佩。李云石在三八线附近坑道里得了病,走路不跟趟,也没条件治疗,在朝鲜牺牲了。薛正俭倒是活着回了国,可惜这伙计回国在骑兵团因一次意外也牺牲了!赵光远大个子,当班长,很上进。黄立佩好汉子,能打能冲能干活,立了三次三等功,真不善!
俺几个伙计都二十上下岁,赵光远和黄立佩才十九岁,面红腮白的小青年呐!正月十四出门的,戴着红纸花、披着红绸子、骑着毛驴子,有板有眼的来。
新兵团先在即墨城集训、学习。有一晚上政府慰问新兵,组织看柳腔戏,看戏的有新兵也有群众,演的是古装《九件衣》,演乔举人致死人命、诬告平民百姓的故事。那两个冤屈的男角女角我忘了叫什么了,打死一个,自尽一个,生怪那个乔举人发坏,还在台子上舞舞乍乍,真把我气急了,我“嘚儿”一下子跳上戏台,上手照着乔举人就俩耳刮子。坏了,闯祸了,人家是演员,我把人打了,这全乱套了!俺排长把我捽(zuó)下来好一顿拾掇,说要把我撵家来。好歹这个事儿过去了,三疃五里的伙计们笑话了我一辈子。
俺在大留村舞旗埠发了军装,步行到胶县火车站,干部、群众夹道欢送。在胶县重新编排连队,俺自己村四个战友打那会儿就分开了。
从胶县车站上火车,坐着“闷罐子”车奔东北。排级干部在门口把门,说是负责安全,晚上要小便,尿在大罐子里,大便呢,蹲在门口儿,排长扯着你,撅腚往外拉呗。到了德州,重新编团,番号是山东警备3团3营8连。一个礼拜之后到辽宁本溪,发了武器。又过了一个礼拜,到了安东(今辽宁丹东)。开动员会,发物资、发服装、准备粮食,忙活了好几天。
5月4号那天,白天休息,傍晚步行过了鸭绿江。
一直走,一直走,都是白天隐蔽,晚上再走,走了七八天。等到了27军77师驻地,我们停下。听说是干后勤,我火了,不是来打仗嘛,拉车子、扛粮食、扛子弹俺还上恁朝鲜来?这干什么吃的!
我就是这么个人,小时候,家里穷,被欺负惯了,老有反抗精神,老想打个仗。当了兵,不上前线打仗,立功杀敌,在后勤部门,我是老大不高兴。我要求去作战部队,排长批评我,说我一波未平一波又起,班长嫌乎我,说我刺儿头。我呢,一路上也看见战场形势了,后勤运输工作真不比前线轻省,罢了,干吧,慢慢也就认定后勤运输这个岗位了。
关于后勤运输,彭德怀司令员有过一个评价,他说:“抗美援朝一半儿的功劳是后勤的,怎么这么说呢?因为在国内作战,政府可以动员解放区运粮,但是,在朝鲜得全靠志愿军自己,后勤运输就是志愿军的生死线。”这话真不假,特别是到了三八线,很明显,后勤运输非常困难!可以用几个字概括“前运弹药,后转伤员”——向前方供应粮食,这是人吃的,但枪炮也得要吃的,你不给它吃饱子弹、炮弹,怎么打胜仗?向后方运伤员,伙计们负伤了,得运回来。
朝鲜大一点的村都叫飞机轰炸了,村里看不见人,都分散开上山逃了。所以,咱部队没有房子住,就睡地铺、山坡和山洞。扫拉块平地儿,油布一铺,就是床。好几块油布连成片,穿上绳线,可以搭成小型帐篷。
粮食和弹药通过大后方火车、汽车一个兵站一个兵站转运过来。沿途高岭上有防空哨,飞机来时提前报警,警戒员“砰”地放声空枪,汽车马上熄灯。物资、粮食到了兵站,往阵地上倒就没有汽车了,不能靠天靠地,全靠运输兵肩扛背驮。前线阵地消耗很大,人要吃,枪炮也要吃,我们白黑夜宿不闲着。为保密,防止特务破坏,我们还学使用代号,比如说前方报过来需要供应多少子弹,说“花生米”,需要多少炸弹,说“苹果”,代号儿多着来,现在老了,记不清了。
俺团负责27军77师的物资运输,27师作战对象是李承晚的韩国兵、美国兵还有印度兵。听说印度兵战斗力差,一打就趴下,笑煞人。
有段时间,3营调到前线,补充到作战部队。这遭我来劲了,营长问我怕不怕,我说,“不怕。”那是在上甘岭,白天黑天,主要是防御,我还真没过过打仗瘾呢。为什么呢,防御也是战斗的一部分嘛,哪像电影上演的光呼通着打?
运输不跟趟,断粮了,光有炒面吃,我们又摊上了毒气弹。因为缺青菜,接近一半战士得了夜盲症。有个土方,煮马尾巴松水喝,很有效。但那个水味道不好,都不想喝,排长就下命令,不喝不行。细菌战很残酷,飞机往下撒传单,战士们用传单纸卷烟抽,用传单擦屁股,没想到,美国人早在传单上面抹上毒药,中毒了,美国佬真坏!连队号召夹毒老鼠,夹三百个就算立功。我觉着三百个耗子太沉了,就剪下耗子尾巴上交,伙计们都说,赵丕山就是聪明。
敌机轰炸,逼着我们过昼夜颠倒的生活,白天睡觉,晚上活动,作息和平常相反,可以称为“夜猫子”。咱的炮兵主要有苏联“喀秋莎”、60炮、76.2野炮。“喀秋莎”炮弹有十二发装一箱的,也有二十四发装一箱的,二十四发装那种两到四个人才可以抬得动,一辆小嘎子车能拉十二箱。六尺长的“喀秋莎”炮弹箱还可以当棺材,用来埋葬牺牲的战友。60炮弹每箱装两发,重量一百六十斤,两个人才能抬得动。76.2炮弹每箱装四发,每人每次可以扛两箱。
第五次战役中,我们2分部主要负责中线战场运输补给。阳德郡和孟山郡在庙山山脉和大峰山山脉之间,仅有一条不算太平的山间公路,是中线运输最重要的交通命脉,但也是敌人的重点轰炸目标。那时,部队运输团很少有防空武器,就靠防空警戒,沿路每公里设一个防空哨。
上甘岭战役打了四十三天,咱都看《上甘岭》电影来,哎呀,现场比电影厉害多了。哎呀,值不说!上甘岭战役期间,俺2分部全力供应第15军弹药和粮食,洪学智副司令员亲自督战。前线需要什么,后方就不惜一切代价运什么。敌机日夜封锁,狂轰滥炸。运输车辆、工兵部队和民工运输队那么多,怎么办?高炮部队发威了,咱有喀秋莎。厉害了,美国飞机没有那么些本事了。
有一次,我看见防空部队使高射机枪作战,两挺伪装的高射机枪架在山岗上,那个架把也挺威风的。其实,高射机枪打飞机是很困难的,高空够不着,低空敌机飞太快,无法瞄准,主要是用来咋呼。听说,他们击落过一架敌机,战士们非常兴奋,跑过去看,欢气得一蹦一跳的。
还有一次,防空部队首长带警卫员和通讯员去察看战况。他们白天上路,傍晚走到半道,没防备被两架敌机瞄上了。情急之下,司机叫跳车,应该从侧面跳,他们不懂,从后面往下跳,结果有两个人撞伤了脚,滚到路边小沟了。车停藏起来,趴在沟里,直到黑天才脱了险。
朝鲜战场确实艰苦,可是我真怀念那段日子,不打仗的空,朝鲜老乡帮咱们捣米,他们经常唱《捣米谣》,那个曲调可好听了,我现在还能哼拉两句——当时唱的是朝鲜话,现在忘了,但我知道意思:“妞儿吃,妞儿尝,妞儿长大去放羊,捣米,放羊,妞儿更比哥儿强……。”老乡跟我们说话,总是一口一个“道木”,是什么意思呢?就是“同志”。朝鲜人都会说些半生不熟的汉语,咱也会些半拉子朝鲜话。比如,我当年向朝鲜老乡讨水喝,就问“一骚”(有没有)?“骚”就是“有”,“奥不骚”就是“没有”。
自打1957年春复员回家种地,我没有一天不寻思朝鲜的事儿。老了,都忘了。不过,有件事没忘,当年抗美援朝耽误解放台湾了。
采访手记:
我是2020年11月30(阴历十月廿五日)采访的赵丕山老人。第二天,笔者去北安街道下疃村采访赵丕山的战友,两位八十九岁的老战士赵光远和黄立佩。他们俩都回忆了一些赵丕山自己没有讲过的战场经历、逸闻趣事,笔者想回头再约赵丕山,让他补述那些故事。没想到,仅仅过去十天,12月9日,老人就过世了。
他儿媳妇纪清华女士在电话上跟我说:你们离开的那天中午,老人说自己心情很好。但我很歉疚,尽管有幸记录下了他抗美援朝的部分故事,但没有了第二次采访,是一大憾事!
我坚持采访这个口齿不清的老兵,记录和整理文稿也吃了些苦头,但我认为很值得。我忘不了他坐在轮椅上侧头倾听的神态,我给他擦过嘴角的涎水,我握紧过他温软的大手,……。
也许,对赵丕山自己而言,唯一的一次接受采访,是生命终点最圆满的记忆。
唯此,宁有缺憾,聊可慰藉! (傅中魁)